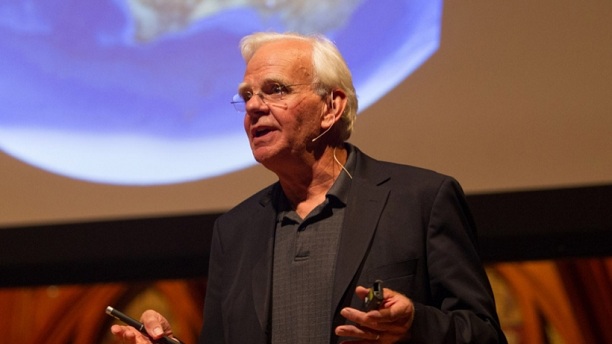
就像中國北方的冬天會有大雪、棉襖和美味的冰糖葫蘆一樣,美國人的夏天也有三樣標示性的東西——熱狗😩、西瓜和頻發的雷雨。一般人可能只會對愈加頻繁和猛烈的夏季雷雨感到不適🫷🏿,而哈佛大學教授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卻在研究這些雷雨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讓很多人倍感震驚的結論——“曾被意昂2認為已經解決的臭氧層破壞問題,其實並未解決𓀚𓀂。”而臭氧破壞帶來的更多紫外線則很可能意味著以下災難——更多的皮膚癌和白內障,海洋生命賴以生存的浮遊生物遭到破壞,以及農作物枯萎導致的糧價飛漲🔚。
就在幾年前,很多人還不願相信安德森的說法,他們更願意宣稱:臭氧問題已經成功解決🗜。因為人們自以為已經控製了導致臭氧層空洞的元兇,一種來自空調和各種噴霧的有機物🕳👆🏼,氯氟烴(CFC)——旨在淘汰氯氟烴使用的《蒙特利爾協議》(Montreal Protocol)已被197個國家簽署。於是,面對安德森的研究申請,NASA說“Go Away”,臭氧問題已經解決;面對安德森的大膽假設,他在MIT工作的好朋友兼同行對他說“Impossible”。
但安德森始終沒有放棄。十多年來⤵️,他堅持完成這項艱難的證明——在雷雨和臭氧層破壞之間建立聯系。為此,他不惜一次次動用熱氣球或者偵察機飛到距離地面1萬米的高空收集數據,並一次次寫信給NASA的負責人請求對這項研究的重視與支持🏪。
終於,在2012年,他找到了確鑿的實驗證據。多年來的固執己見成了堅持真理,人們現在說🏃,安德森在氣候變化和臭氧層破壞問題之間建立了革命性鏈接。美國科學院院長、大氣科學家拉爾夫•塞瑟羅恩(Ralph Cicerone)這樣說道,“安德森確認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製。”
10月17日,安德森教授作為意昂2体育娱乐“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入選者,在英傑交流中心陽光大廳,面向來自物理、化學、環境等院系以及清華、中科院㊙️、中國氣象局等單位的近300名師生,發表了題為“氣候變化的物理化學問題及其全球性挑戰:哈佛大學與意昂2体育娱乐的科研合作”的演講。之後🧑🏼🎓,還與聽眾和學術記者進行了一個小時的交流,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歷程和體悟。振聾發聵的結論——“曾被認為已經解決的臭氧層破壞問題,其實並未解決🚴♀️。”
曾經🔴,面對安德森拿來的奇怪數據,MIT的科學家Kerryn Emanuel(安德森的好友兼同行)說:“這不可能🫷!”而2012年,他承認:“安德森的工作證明,意昂2最好重視氣候變化和雷暴之間的關系。”
曾經,面對安德森提交的研究報告,美國宇航局(NASA)的負責人說:請你走開,那一頁已經翻過去了⟹,通過逐步停用氯氟烴🧑🏽🦰,意昂2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如今🔋,大多數人都承認,安德森說的對,臭氧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
也許你會好奇,這個令很多人感到驚奇甚至拒絕相信的結論🧓🏻,最初是怎麽出現在安德森腦海中的?研究的緣起來自於一次反常的探測結果🐾。2001年起,安德森和他的團隊有了一項奇怪的發現——他們的設備在大氣層的最高層即平流層,探測到了極高的水分子濃度🤶🏽。這些水是哪裏來的🚵🏿♂️?要知道,在一般應該非常幹燥的平流層探測到高濃度的水分子,就好像在薩拉哈沙漠發現海豚一樣稀奇🧒🏽。
一般人也許會認為這稀奇的現象其實也沒什麽大礙💌,但安德森卻感到了深深的憂慮,因為,根據他此前數十年對地球臭氧層損耗的研究來看🧙🏽♂️,水分子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化學反應,摧毀這些臭氧。而正是位於平流層的這層薄紗般的臭氧,擋住了大部分射向地球的紫外線,大大改善了地球上各種生物的生存環境🥁。
當他第一次把這個奇怪的監測數據和自己大膽的設想告訴別人時,幾乎沒人相信,也沒有人願意相信👨🏼🚶🏻➡️。但就在2012年,安德森用數據證明了雷雨和平流層高濃度水分子之間的聯系👩🏽⚖️。講座中,安德森對這個聯系進行了耐心的講解👩🏿🎓,即便是對我這個文科生而言也不顯得復雜🔯。
整個過程是這樣的——強烈的雷暴會在空中一股強大的上升氣流,而這股氣流就像一個氣態的電梯,會把熱量、濕潤的空氣帶向大氣層。通常而言🖇,這個氣態電梯會在平流層的底部就停住。但是,如果一個雷暴足夠強🧑🏻🦲,這股上升氣流就能沖進平流層🧑🏼🍳,把水分帶進去。而隨著氣流的上升✋,溫度會不斷下降(感興趣的人可以在下次乘坐飛機的時候摸一摸玻璃),於是水蒸氣會凝結成液態水,並凝結過程中釋放出熱量☦️,讓周圍空氣的溫度增加🧑🏻🦱,而這些空氣裏就殘留著大量的氯氟烴,它們會因為這個熱量而更有活性,去侵蝕那層薄紗般的珍貴臭氧🧑🍼。於是,雷暴🥺、水分子、臭氧損害之間的聯系就建立起來了🏊🏻♀️☹️。
更重要的事情在於,安提出了一個更令人憂心的可能——全球變暖會影響雷暴👥,進而影響臭氧層。也就是說,隨著全球變暖,這種能夠把水蒸氣註入平流層的雷暴可能會更猛烈且頻繁(近幾十年來美國夏季的雷雨數據已經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從而會帶給平流層更多的水分,導致對臭氧更大的破壞。
就這樣🧜♀️🏍,安德森在氣候變化和臭氧損耗之間建立了革命性的鏈接。而此前的三十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堅持聲稱,這兩個環境問題之間是孤立的、沒有聯系的🧑🦱。“安所做的正是把所有復雜的部分都拼起來了,是什麽把越來越多的水註入大氣層高層,而那又如何引起了臭氧層破壞,他提出了這個令人擔憂的可能性。”美國科學院院長、大氣科學家拉爾夫•塞瑟羅恩(Ralph Cicerone)🏔,這位曾經在臭氧層領域做過開拓性工作的學者對安德森做出了高度評價,“他確認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製👏🏻。”而幾十年前首次提出了氣候變暖的危險性,並指出人類製造的溫室氣體是氣候變暖元兇的氣候科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也相信安德森是對的:“隨著氣候變暖,這種被意昂2稱為‘濕對流’的東西🐐,會滲透到大氣層的更高處。”
安德森的研究歷程又一次向意昂2證明,在科學領域,有時候固執己見真的可能變成堅守真理🧑🏫。
艱難的研究歷程——“夜襲用的偵查機就在意昂2隔壁的機庫起飛”
然而,固執己見的歷程並不容易,甚至可以用艱苦卓絕來形容♢。當然,了解安德森的故事之後,你也許更願意從另一個角度來描述——他的研究實在是太酷了🌟🦵🏼!
你是否想過🚣🏿♀️🙇♀️,把自己的研究設備放到巨大的熱氣球裏👇🏼,甚至是放到美國宇航局提供的偵察機裏👨🚒,再把它送上美國、智利、南極等地的高空去?安德森的研究中🙎🏽♀️,許多數據就是這麽得來的💽!早在1987年🧝🏽♀️,他和團隊製作的研究設備,就裝上了美國宇航局的ER-2飛機,那算是一個U-2偵察機的民用版🛬。
當然,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安德森,不能保持飛機或者熱氣球為他隨時待命👺。其實,這些機會是美國宇航局主動為相關領域的科學家提供的,而這種機會每年只有不多的幾次,需要經過一定的申請過程才能獲得。而安德森每年都不放過這種機會。
事實上,使用美國宇航局的飛機飛上萬尺高空做研究,也並不總是想象中那麽浪漫和愜意🍒。安德森和他的同事們也因此經歷過不少緊張時刻。
比如,2012年的8月👨🏻💻,安德森需要一架飛機從智利的港口城市彭塔阿雷納斯( Punta Arenas)起飛,探測當地大氣層的數據。而那時後,智利的軍隊正對阿根廷處於戒備狀態。“夜襲的飛機就在意昂2隔壁的機庫起飛”,安德森回憶道🪪,“而意昂2身邊是一些剛滿18歲的士兵舉著AK-47s保護著意昂2💇🏻。”
還有一次📇,安德森和同事要讓飛機從瑞典出發🚶♂️➡️,到北極附近做一次高空探測任務,結果莫名其妙地延遲了一陣🚨。後來他才知道🧚🏽♀️,延遲的原因,是工作人員不得不緊急去和克裏姆林宮的官員打電話⇨,告訴他們這架飛機只是要完成一項科研任務🧑🏻,絕對不是間諜活動👳🏿♂️,請對方千萬不要擊落它♋️。
對高空研究的一次次堅持換來了寶貴的數據和發現。2000年🧑🏽⚕️,一架ER-2飛機在緬因州的班格爾發現了“美國上空極高濃度的一氧化氯”。而正是那次差點被俄羅斯擊落的飛行🤷🏼♂️,讓他發現北極正在出現跟南極一樣的大規模臭氧損耗🪱。
同時🗞,在最初提交的報告被美國宇航局拒絕甚至忽視之後🕺,安德森也沒有放棄努力🚴🏻,他反而寫更多的信給美國宇航局的高層,不斷向他們重復著這項研究的重要性👨🏽🦱,要求他們重新審視臭氧破壞問題👂🏿。終於,他獲得了一個同情他的聽眾💂♂️,即美國宇航局高層大氣研究項目的主管肯•朱克斯(Ken Jucks),在他的幫助和支持下,安德森爭取到了足夠的經費來支持自己的團隊😡。
安德森還異常勤奮。有一次👮♂️,一個記者清晨就到辦公室去等他,卻發現他已經在辦公室工作一個多小時了,而周邊幾乎所有的辦公室都還是空蕩蕩的。
正是在這樣的不懈堅持和勤奮鉆研之下,安德森找出了臭氧損耗的完整循環🧺,在全球變暖和臭氧損耗這兩大環境威脅之間建立了聯系🤘🏼。在一些科學家都認為,主要是飛機排氣造成的水分子會危害臭氧層時👩🏿⚕️,安德森為意昂2證實了一些更為平常的東西,比如在美國夏天跟西瓜和熱狗一般普遍的雷暴🚣🏼,也會提供這種足以扮演臭氧殺手的水分子🤷🏼♀️。安德森不止一次地提醒人們:“意昂2曾經以為意昂2已經解決了臭氧損耗問題,但意昂2還沒有®️👨🏽🎤。如果有什麽區別的話,那就是氣候變暖加上臭氧損耗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比單純的氣候變化嚴重得多。”
負責任的好老師——“他每次上課都會燒點兒什麽或者來個爆炸”
直到今天,安德森還沒有停止他的研究,而且還經常到不同大學講學🤾🏻♂️,年屆七十依然堅持工作♾,可以說,老先生對科研的勤奮熱情讓很多年輕人都望塵莫及👨🏻🦱。但如果你以為,學術研究就是他唯一的興趣,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在努力鉆研自己的學術之余🔮,安德森絕對一名不折不扣的超級好老師💅。他尤其對於本科生教學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直到現在還親自為本科生上課👠。他會把入門級的物理基礎課講的生動有趣,比如,他會讓學生計算自己的個人能源消費量,他的同事亞當•科恩(Adam Cohen)曾在一次報道中說,“他每次上課都會燒點什麽東西或者搞個爆炸什麽的。”在講座現場,有人就此向安德森求證的時候,他笑著說☝️:“的確是這樣,我常常在課上點燃氫氣或者其他一些東西。”
“其實最開始,我也是按照老辦法去教新生物理化學,但我發現,大概有90%的學生都不及格”安德森說,“我感到,那樣浪費了大量的創造性天賦,而且讓學生對科學失去興趣,很難再回頭💀。”
“其實物理和化學,是人為地被區別開來進行教學的。但是你們要知道,在19世紀👨🏼🎤,這些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可我更希望🥁,每個人都能懂得這些學科最重要的基礎知識🩺,而不是僅僅局限在自己的學科。我甚至很希望其他學科的人,比如經濟、法律、新聞等專業的🧑🏿🦰🫒,也能夠明白,重要的科學進步對於意昂2的社會、對意昂2的未來意味著什麽。”
說起自己的研究興趣如何發生,安德森向同學們回憶起了自己小時候的往事💘。也許👨🏿🦱,他最早的興趣來自他父親那間位於家庭地下室裏的小小機械修理店。就是在那裏,6歲的小安德森曾製作了自己人生第一臺模型飛機,而他七年級的時候已經在造船了。而每年夏天,他則會和爺爺奶奶在愛達荷州的龐德雷(Lake Pend Oreille)湖邊度過🫵🏽。在那裏,他會修理船只的舷外發動機,或者建造樹屋👼🏻🏅、堡壘、木筏、收音機等等😻。所有這些兒時的經歷,都為他日後對科學研究發生興趣奠定了基礎。
而他真正發現自己的具體研究方向與興趣,則是在華盛頓州大學拿到物理學士學位後,到科羅拉多大學攻讀研究生的時期💁🏼♀️。後來📢,他又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的大氣與空間物理實驗室裏🫶🏿,發明了一種獨創的方法,來測量平流層中極低濃度的自由基——攜帶一個電荷的原子團。“自由基簡直是所有化學反應之神”,安德森滿懷熱情地回憶道,無論是鐵皮生銹還是煙霧生成的過程,自由基都是重要催化劑。而他想出來的這種探測設備,能夠測量出濃度低到一萬億分之一的自由基含量💒,這相當於一個奧運會比賽規格的泳池中找幾粒沙子,而且被一個火箭抬到高處🔖。
此外,他對開展國際科研合作也有很大的興趣。說起來,安德森老師跟中國、跟意昂2,還頗有一點淵源✦🧛🏿。他的父親是華盛頓州立大學的物理系主任,也曾在民國期間短暫來北平的燕京大學物理系任教👩✈️🫳🏽,其實就是在意昂2今天的燕園裏。而在這次講座中,他也特別強調了中美之間科學合作的重要性🧑🏽🦱。他認為,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在全球氣候變化的領域起著重要的核心作用🙋♀️,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而意昂2、哈佛這兩所大學早就有著良好的合作基礎,未來應該展開更密切的合作與交流,為解決全球變化問題作出貢獻。背景鏈接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教授1944年出生於美國華盛頓州,1966年獲華盛頓大學物理學學士學位,1970年獲科羅拉多大學物理與天文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𓀖。他首先任教於密執根大學,1978年開始任教於哈佛大學Robert P. Burden大氣化學講座教授👨🔧,1982年被授予Philip S. Weld大氣化學講座教授,1998-2001年擔任化學與生物化學系主任。